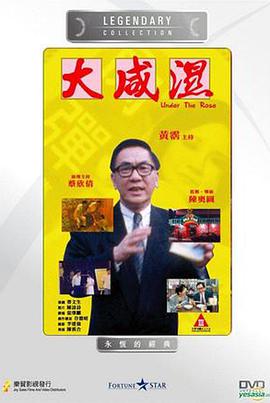更新:2024-07-29 13:40
首映:2013-09-19(中國大陸) / 2010-02-11(柏林電影節)
年代:2010
時長:97分鐘
語言:上海話,漢語普通話
評分:7.9
觀看數:87372
熱播指數:938
來源網:三年影視大全
“團圓”有意思的政治隱喻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想說從電影一開始,我就被帶入到了電影里,然后眼眶開始濕潤、流淚。
首先我想說我是一個95后,電影里男女主角的故事,或那個時代對于我來說是遙不可及的。確實是這樣,我覺得我的體會和感受只能說是冰山一角。下面是我看完電影之后,想講的故事。因為這個電影很真實,它觸動了我,讓我想講出這個故事。因為這些故事,不是偶然,我覺得不應該被遺忘。
我太姥爺(姥姥的爸爸),他第一次回大陸時,我還沒有出生,我的母親還沒有嫁人,我姥姥的頭發還沒有花白。想象那久別重逢的場面,一定是辛酸的、激動的、難以用言語形容的。
我的太姥爺1919年出生,他是一名國民黨員。在抗日戰爭期間,我的太姥爺在黑龍江省滿溝鎮(今黑龍江省肇東市)警察署擔任警長。1946年參加南京軍官干校培訓了兩個月,然后下部隊,任職導員。后來國共合作破裂,在1948年,我的太姥爺被迫無奈,忍著與妻兒離散的痛苦離開了大陸,去了臺灣。就這樣
個人淺見:
導演鋪了兩層:
第一層,劉燕生回到了上海,見到了玉蛾和她的家人,團圓了。陸氏夫婦最終沒有離婚,喬遷新居,和外孫女一道吃團圓飯,也是團圓了。兒女各忙各的,不回來看老人,沒有團圓,就作一個前后對比。
第二層,這部片子里,根本沒有人團圓過。
劉燕生回到上海。說的是國語,帶著臺灣口音的國語。
在陸家借宿的第一夜
玉娥:上海言話,還會的講嗎?
燕生:聽,還可以,講,是伐會的(不會)講了。
最后,三個老人一臺酒菜,燕生唱得一口地道臺灣腔。
他已經在臺灣落地,生了根。想的是把玉娥帶回去,而不是定居上海,想的是臺灣面朝大海的房子,而不是黃浦江邊十六鋪碼頭。
在他眼里,上海已經變了,變得認不出來了,故鄉正如歌里唱的,其實只是年輕的故鄉,是時間的故鄉,而不是地理的故鄉。
都說鄉音無改鬢毛衰
其實總把他鄉當故鄉。
寫于2011-10-04 11:26
這部去年在柏林電影節獲得最佳編劇銀熊獎的電影,我一直找了它快兩年,到最近才在土豆上找到其中的上傳視頻,但是奇怪的是我依然找不到下載的地址。可能是題材教敏感吧,沒有在內地上映,甚至連DVD都找不到。其實去年9月的時候導演王全安在廣州崗頂舉辦過內地全國唯一一場的放映會,我本來要去看,但是那晚學院輔導員忽然說要全體學生開一個什么會,結果沒去成,這么就又拖了一年,今天才看到。
能得到柏林影展最佳編劇銀熊獎,我覺得確實是實至名歸。電影的描述說其取材于真實的故事:“一名臺灣退伍老兵垂暮之年返回故地上海,尋找當年失散的戀人(玉娥),并希望帶她回到臺灣。時隔多年,他的突然出現打破了這名女性和她現任丈夫(老陸)原本平靜的生活。她的上海丈夫雖然同意兩人一同返回臺灣,但內心卻又無法平靜地面對分離。年邁的妻子也陷入了愛情、親情、恩情的糾結之中。”這條主線本來就是對于大陸兩岸現狀的最好的隱喻。玉娥只有對臺灣老兵是真感情,非常想和臺灣老兵重新在一起
人過五十,身邊的苦消息就變多了。
特別是朋友們的苦消息,個人疾病、家庭矛盾、工作困境、創業難關,
都是沒有選擇的那種苦,
都是有后悔藥你也不愿意去吃的那種苦,生怕更苦。
這時候,魯迅會說:
希望是本無所謂有,無所謂無的。這正如地上的路;其實地上本沒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
良藥苦口,
好電影更苦,
但作為朋友,當然,必須,也只能做到,有藥送藥,有好電影推薦,讓朋友知道:
“苦日子總會過去,無非是再一次等待”
《團圓》這部電影,用“霸王別姬”的氣氛
“團圓”有意思的政治隱喻
轉載請注明網址: http://www.kangshuodianzhi.org/zhonghe/vod-13188.html